男女主角分别是刘清宁王静的其他类型小说《两万里路云和月刘清宁王静后续+全文》,由网络作家“茹若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云林镇上,横跨东西的长街是最热闹的。长街不长,只有几百米,副食品店,五金店,菜市场,小饭馆,热闹的时候,从街头开到街尾,整整一条街的店面。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,这些年镇里人口不断减少,电商快递又发达,许多店面都开不下去,纷纷倒闭,有几年连菜市场都倒闭了,要买好货得坐半个小时公交,到隔壁镇上去买。直到去年市里的企业投了钱,才又重新开出来。吴兰香的兰香面馆在这条街上却是屹立不倒。长街的东头是镇政府大院,兰香面馆开在西头。镇里的干部有时吃腻了食堂,或者下村回来过了饭点,就到兰香面馆里吃碗面,吃饱了沿着长街走到东头,刚好消食。面馆的西面就是清源溪,溪上一座石板桥,桥头两棵千年古樟,樟树底下就是镇里人讲闲谈的地方。这两天镇里人闲谈里讲的最多的...
《两万里路云和月刘清宁王静后续+全文》精彩片段
云林镇上,横跨东西的长街是最热闹的。
长街不长,只有几百米,副食品店,五金店,菜市场,小饭馆,热闹的时候,从街头开到街尾,整整一条街的店面。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,这些年镇里人口不断减少,电商快递又发达,许多店面都开不下去,纷纷倒闭,有几年连菜市场都倒闭了,要买好货得坐半个小时公交,到隔壁镇上去买。直到去年市里的企业投了钱,才又重新开出来。
吴兰香的兰香面馆在这条街上却是屹立不倒。
长街的东头是镇政府大院,兰香面馆开在西头。镇里的干部有时吃腻了食堂,或者下村回来过了饭点,就到兰香面馆里吃碗面,吃饱了沿着长街走到东头,刚好消食。
面馆的西面就是清源溪,溪上一座石板桥,桥头两棵千年古樟,樟树底下就是镇里人讲闲谈的地方。
这两天镇里人闲谈里讲的最多的,就是前些天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回来的王永梅老嬢嬢。昨天她已经出院了,在美莲家住几天。前天去探,看起来红光满面,竟比住院前精神气还要好。
听说是老嬢嬢那个去了马德里十多年的小外孙女回来了,说要留下来照顾老嬢嬢养老,还要带老嬢嬢搬回云上村老屋去。
难怪老嬢嬢精神头这么足。那丽琴可称心了。
云上村现在还有人住?
怎么没人住,李阿四不就住在村里?还有那个——
说话的人朝着兰香面馆的招牌使了使眼色,对方便懂了。哦,还有老吴头也在云上村住着嘞!
兰香坐在面馆门前默默地摘着豆芽,没作声,悄悄往店里看了一眼,侄子吴鑫正埋头吃面。
那人又问,云上村的老房子还能住?风吹雨打,都烂了。
修啊。
那后生囡有这么多钱?
她没有,向高有嘛!
李丽琴骑着电瓶车从石桥上路过,那些议论声立刻就停了。她装作没事,慢悠悠从一众人面前过去,等拐了弯,才一拧把手,加速冲回家里,将菜篮子往地上一丢,倒了一碗热茶,咕噜噜灌下去,坐在长凳上生闷气。
生什么气呢?
闹这一场,不就是想要甩掉老嬢嬢这个烫手山芋。现在有人接手了,她该称心了才是。可镇上人风言风语,当面不说,背后戳她脊梁骨。
这些天,她连自家开的小超市都不敢去。
从街头走到街尾,那些针扎一样的眼光仿佛无处不在。
王向远呢?
从前每天晚上准时十点关门回来睡觉,现在在仓库支了张床,干脆睡在了店里。她回来小半个月,两夫妻愣没见上几面。
远在外地的大女儿打电话回来,直骂她糊涂。
老嬢嬢一把老骨头,还能活几年?忍一忍就过去了,落个好名声。还好老嬢嬢没事,不然大姨能善罢甘休?闹了这么一场,把大姨得罪了,以后家里有什么事,怎么开口托她去办?
李丽琴又悔,又恨,又庆幸。
老嬢嬢出院前,王美莲带着阿宁囡囡,叫上了村长,来了她家一趟。
白纸黑字要她签字,讲明把山上老屋写给老三,往后拆也好建也好,一概与她无关。同意,老嬢嬢再不要她管。
李丽琴没犹豫,签了。
骂已经挨了,何必到这时候假惺惺。
王静没料到,这一趟回国是两个人来,一个人走。
当她得知刘清宁私底下给小舅妈打了电话,说服她掏了五万又借了五万,用来修老屋的时候,十万块已经存进了刘清宁拿着刚刚办好的中国身份证开的银行户口。
办事干脆利落的速度,让她不禁怀疑自己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女儿。
“瞎胡闹!那破房子修起来有什么用?这,我怎么跟万信说去?”
她每日拉着王美莲嘟嘟囔囔,最后王美莲也烦了,劝她:“儿大不由娘,她都长大了,你能拿她怎么办?总不能把她绑上飞机。就算回去了,她自己也能买机票飞回来。你看我家楚楚,现在我说十句话,她能有一句听的,都算孝顺了。”
说着狠狠剜了横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吴楚楚一眼。
吴楚楚悠闲地晃着脚丫子,嘿嘿笑。她心想起那天刘清宁说的话——自己做的选择才有资格说后悔。
如今她们都已经长成了能做选择,能承担选择后果的年纪。
回马德里那一天,王美莲一家人和刘清宁陪王静去的浦东机场,王静铁青着脸,一路上一言不发,等到了闸口,终于还是动了容流了泪。
“在中国有事情,记得去找你大姨。”
“嗯。”
“记得常给妈妈打电话,发视频。”王静叮嘱着,心里却知道,即便有事,刘清宁也是宁可和吴楚楚说,怎么也不会找她这个妈妈。
“知道了。”
“行了,快值机吧!这一张国际机票可好几千呢!别误机了!”吴楚楚催促着。
王美莲骂:“你就不能说点能听的话!”
“这机票不能退改签的!”
“闭嘴!”
“我说的是实话!”
“哎呀你够了!”
看着王美莲和吴楚楚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嘴,再看看拘谨地与自己保持着距离的女儿,王静知道,自己这辈子都不能和这个女儿像那般亲密了。
“妈妈走了。”她伸手,拍了拍女儿的手臂。有那么一瞬间,她有一种冲动,想要抱抱女儿,可最终还是没有抱。
她敏锐地感觉到,刘清宁察觉到她想要拥抱的意图,已经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心里一酸。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抱过这个女儿了,上一次......还是被包在包被里的时候,小小的圆圆的脸,冲着自己笑......
“好好照顾自己,多吃饭,多穿衣。”
“好。”刘清宁仍旧是点点头。
吴楚楚在旁边嘀咕:“马上就夏天了,热死。”
话音未落就挨了王美莲一个“五股栗”,捂着脑袋到刘清宁身后。
王静挥挥手,不再说话。
刘清宁静静地看着王静消失在安检口。
“有舍不得吗?”吴楚楚小声问。
刘清宁细细体会了一下,摇摇头:“好像并没有。”
心里有几股复杂的情绪交织,但细细抽剥,却没有一股叫“不舍”的。
从浦东机场出来的时候,正好有一架飞机起飞,庞然巨物轰鸣着从头顶飞过。
刘清宁望着那飞机,十三年前,她在这里第一次坐飞机,带着对“家”的憧憬远渡重洋,但迎接她的却是陌生与失望。如今,她在这里挥别母亲,仿佛对过去十几年的自己做了个告别。
再见,马德里。
临近清明,淅淅沥沥地下了半个月的春雨,真到了清明时节,天却放晴了。
清晨,薄雾弥漫在瓯江上。
张阿婆凌晨就起来忙乎,天刚擦亮就把摊子摆了出来,占据了华侨酒店门口最佳的位置。
虽是清晨,酒店大堂却并不安静,间或有远道而归的出租车在大堂停下,下来两三个风尘仆仆的乘客,卸下三四个塞得鼓鼓囊、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的红白蓝编织袋。
张阿婆的儿子儿媳妇都在华侨酒店上班,说这前后半个多月,城里的酒店全满了,住的都是从国外赶回来扫墓祭祖的华侨人,小两口天天忙得脚不着地,加班到半夜才回家。
回来好,回来好啊。
这城里乡下的,不都热闹起来了吗,她的萝卜丝饼摊子不就忙活起来了吗。
这青田城里乡下,一年到头最热闹的,除了过年就是清明,也是她的萝卜丝饼摊子生意最好的时候。
张阿婆年纪虽大,但耳朵还灵,尤其是听到手机时不时地响起:“微信到账XX元支付宝到账XX元”的时候,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
又一辆出租车在酒店大堂前停下,下来两个女人,像是两母女。一对等在大堂门口的中年夫妻急忙迎了上去,帮着从出租车上卸下整整五大袋行李,手忙脚乱地往明亮的大堂里拖去。
年轻的女人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,没有急着跟进去,反而裹了裹风衣,打量起周围的环境。目光在街道上逡巡了一圈,最终落在她的萝卜丝饼摊子上。
迟疑片刻,女人还是裹着风衣过来了。
四月的早晨还凉,刘清宁裹紧了风衣,迟疑地开口:“一个萝卜丝饼。”
张阿婆麻利地掂起大圆勺子:“蛋要吗?”
“要。”
乳白色的面糊倒进油锅里炸热的大铁勺里一滚,再放进油锅略炸几秒定型,掂起勺子,铺上萝卜丝、瘦肉碎,再敲一个鸡蛋,压实后盖上面糊,送进油锅里炸。
“哪回来的?”张阿婆随口拉家常。
“马德里。”
张阿婆点头:“哦,马德里啊。我小儿子以前也在马德里,这几年去罗马了。”
说话的功夫,一个炸得焦脆香酥的萝卜丝饼便出锅了,放在油锅上方的铁丝架子里凉却滤油后装进油纸袋:“八块。”
小时候才五毛钱一个呢。
刚炸出来的饼,油香,酥脆,一口咬下去,油香裹着萝卜丝的清甜在嘴里嚼碎混合,还未冷却便顺着食道落到胃里,这份熨帖是那些干巴的欧式面包给不了她这颗中国胃的。
她裹了裹身上皱巴巴的风衣,捧着烫手的萝卜丝饼,目光所及之处,浓雾渐渐散去。在飞机上睡了十几个小时,从上海到青田的这一路,刘清宁却清醒得很。眼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从繁华的上海都市到寂静的脉脉青山,天上的星光淡下去,天边透出微弱的曦光,横亘瓯江的太鹤大桥在清晨的江雾里若隐若现。
此时,太鹤大桥在缭绕的雾气中逐渐清晰。
陌生又熟悉。她已经有些想不起来这桥从前的样子,是一贯如此还是重新修整过了?
离开青田的时候她十二岁,如今归来却已经二十五了。
十三年前,她坐上飞往马德里的飞机时,未曾想过自己离开这么多年。
前几年是因为年纪小,没有父母的陪同无法单独回国,后来习惯了马德里的衣食住行,便渐渐地也没了念头。
父母店里忙走不开,她学业忙走不开。总想着来日方长,以后有的是机会回国,等一等,再等一等,明年吧......但没料到的是,有的人却等不了。
外公走的时候,家里的超市还没开起来,条件还不好,父母都在华人老板的商店里打工,请不起假也买不起来回的机票。没能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,母亲王静在电话里对着大姨痛哭了一场。
后来攒了点钱,父母开了个小超市,条件便好起来了。
外公走后,外婆的身体便渐渐大不如前,趁着这次清明,王静下定决心回国一趟,除了给扫墓之外,也是要再在母亲面前尽尽孝。
天边破晓,天也渐渐亮起来。
刘清宁躺在酒店柔软的床上,瞪着眼睛看天花板,身体倦困,可意识却随着落地窗外逐渐亮起的日光而清醒起来,耳朵里飘进大姨王美莲和妈妈王静的低声私语。
“吵得厉害,已经回娘家好几天了。我上了好几回门,面都不见。”
“怎么这样?那妈现在呢?”
“二哥看着呗,没办法。保姆也不好请,老嬢嬢脾气倔,请了几个都做不久。”
“那怎么行,二哥一个男人,怎么会照顾人?”
“那没办法。我让她到我这住,第二天就把东西收拾起来说要走,住不牢!”
“城里面她哪住得牢!”
“那没办法呀!”
这说的是刘清宁的二舅和二舅妈。据刘清宁所知,二舅家闹“家变”已经闹了小半年了,王美莲每每跟王静通视频电话,都要讲到这个事情,唉声叹气一番之后,又要把二舅妈一些陈年烂谷子的事情捯出来说一遍,导致那些故事刘清宁已经倒背如流,对二舅妈也没什么好印象。
二舅王向远年逾六十,原本也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,谁知道这两年国家放开计划生育,两个儿子响应国家号召,前后脚怀了二胎。
大儿子一家住在市里,二儿子一家住在县城,二舅妈李丽琴照顾两个儿媳的孕期,原本就是顺得哥情失嫂意,焦头烂额,偏偏不久前刘清宁的外婆又病了一场进了医院,病床边上离不开人,二舅在村子里开着一间小超市,吃穿全靠这点收入,照顾病人的活自然落在李丽琴的头上,结果两个儿媳妇又闹了矛盾,含沙射影地发了几个朋友圈,李丽琴一气之下撂挑子跑回了娘家。
手机铃声响起,聊天的声音戛然而止。王美莲接起电话,才喂了一声,随即“啊呀“一声惊叫起来。在这静谧的清晨,这惊叫声像一把利刀子,将刘清宁刚刚袭来的困意瞬间划破。还不等她听清楚,房间里便嘈杂喧哗起来,三个长辈的声音此起彼伏,混乱得如同一团乱麻。
王静匆匆把手机塞进随身携带的小包。
“妈,怎么了?”刘清宁压低声音问。
王静半秒都没停留:“你外婆喝药自杀了!”话音未落,三个人带着慌乱消失在客房门外。
刘清宁茫然了几秒,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纸板婆膝下三个女儿,要说多孝顺,实在称不上。纸板婆捡了一辈子纸板,没什么积蓄,最担心的事就是有一天自己病倒了没人管。
“那天你说像你外婆这样的老嬢嬢,老了没点钱傍身是很可怜的,就这么一句话,我就想到突破口了。我对她说,久病床前无孝子,现在三个女儿对你都一般,等你干不动了,还指望她们守在床前给你端茶送水?想想绢花阿婆的事!”
隔壁万山村的绢花阿婆,刘清宁听王美莲对王静提过,就是二舅妈李丽琴的母亲。今年年初,一个清晨,在村道上被镇里收垃圾的农用三轮车撞死了。
提起这事,王美莲骂得可难听,说这一家儿女,全是昧良心的。丽琴那个大哥更是个畜生,自己的老娘,病了不给看病,饿了不让吃饭,老嬢嬢饿得半夜去垃圾堆里翻吃的,才被三轮车撞死了。
这一下说到了纸板婆的心坎里,又抹起了眼泪:“那有什么办法呢,哎,我命苦哦,领导!不像你们,吃国家饭的,我命苦。”
“怎么没办法?只要你口袋里有钱,你还怕她们不伺候你?抢都来不及!”
“我,我哪有钱?”
“是啊,她哪有钱?”刘清宁疑惑了。难不成也像“老屋修复计划”一样,政府给她拨了一笔钱?
陈今越告诉纸板婆,按征地政策,她家户口底下几口人,只能分到一块宅基地,盖一栋楼,这是绝对改不了的。
但宅基地的位置,可以改。
“我告诉她,我去帮她做工作,在她家分到的位置边上,另外规划出一条路来,这样她就有了一个两面开的门面。将来我们镇里是要大搞旅游业的,到时候她在这里开个小卖部,赚点小钱不是问题。就算自己做不动,租给别人,租金也比中间户要高些。自己手里有钱,比看儿女良心要可靠得多。”
这话不好听,却是实话。
“她就答应了?”
“她还有犹豫,说回去考虑考虑。我又说,她要是同意,我立刻去办,她要是不同意,那就耗着。将来换了人,她想同意都来不及了。”
就这么半骗半吓,纸板婆点了头。
“难怪镇里人都夸你脑子灵活,还真是。”刘清宁感叹。
陈今越挠挠眉:“一点小聪明,不值一提。不过解决了这事,老钟心情大好,云上村的事他才肯松口点头,否则你那十万块补贴还没这么容易拿呢,所以这钱是你该拿的,不必谢我。”
“你那哪是小聪明?吴楚楚跟我说,你上学的时候成绩就很好,高考上的还是重点大学。说你毕业了在杭州上班,年薪七位数,不知道为什么又回来了,到这个山沟沟里来吃苦。”
“咳,以讹传讹,没到七位数。”
“那也不少了。”
“她还说了什么?”
“她说你的脑子可灵着呢,到基层来肯定要做出点成绩的。纸板婆的事不算什么,云上村的项目要真能搞成了,那就是你实打实的功绩。她还说你是县里相亲圈的至尊VIP,县里年纪相当的白富美都跟你相过亲......”
陈今越原本听得十分得意,双脚抵着脚后跟,靠在竹椅子上,有一下没一下地往后仰着。他向来知道镇上、县里关于他的传言很多,夸赞很多,或虚或实,从前不觉得在意,可是从刘清宁的嘴里说出来,耳根子竟然有些发烫,直到这句“相亲圈里的至尊VIP”出来,脚下一顿,人往后一仰,险些没被茶水呛到。
“她这是造谣!”他跳起来,狼狈地掸了掸身上的茶水,想了想,又笑起来:“没想到你们俩姐妹私底下倒没少聊我。”
这下轮到刘清宁的耳根子烫了。
一轮明月从东边爬上来,淡淡地挂在山间。
远山浓淡错落。
煤球炉上的水壶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泡,伴着夏日的虫鸣,村子里静悄悄的。
喝了一肚子的茶,这会儿又觉得渴,陈今越轻咳一声,自己去倒茶。刚满上,还未晾凉,就听见远处传来一阵狗吠。
陈今越皱眉。
有事。
云上村养着七八只狗。
与其说养,倒不如说住着七八只野狗,都是周边村镇里跑出来的,到了云上村,村里老人常给点大肉骨头,便在这里长住。
这些狗白日在周围的山头玩耍,夜里聚回村里睡觉。因为是野狗,警觉性很强,稍有点风吹草动便会发出警报。
两人着朝狗吠的方向跑去,跑得近了,才听见有人呼救:“救命,救命!”
陈今越神色凝重,抄近路翻了几座矮墙,很快消失在夜色里。刘清宁看得目瞪口呆,连忙加快了脚步。
半路上撞见抄着扫帚跑出来的李阿四:“怎么了怎么了?哪里出事了?”
“像是荷花池那边。”
“走!”
荷花池在村子的西南角,很大,足有两亩地。原本荒了多年,全是淤泥堆积,前些日子村容整治,镇里派了辆挖机,清出去几卡车的淤泥。
如今池水清清,碧波盈盈,映着月色银光。
刘清宁和李阿四赶到,陈今越已经把掉进荷花池的人捞了出来,两人浑身上下湿透,坐在地上喘气。
七八只大狗围在不远处,仍旧保持着警惕。
被捞上来的是个男人,衣着打扮不像坏人,看着那几只蓄势待发的大狗,抓住陈今越哇哇大叫:“起开,起开,我怕狗!”
是西班牙语。
这男人亚洲面孔,危难时脱口而出的却是西班牙语。
“你没事吧?”刘清宁用西班牙语问道,“别害怕,这些狗不会攻击你。”
那男人听见,脸上立刻流露出“他乡遇故知”的神情来:“太好了,太好了!上帝!你是西班牙人?”旋即又觉得不对,又改口:“你会西班牙语?”
“我是西班牙华侨。”刘清宁说道。
“太好了,我得救了!”男人长松一口气,将裹满泥浆的登山鞋脱了,彻底瘫坐在了地上,仍旧用西班牙语对刘清宁说道:“我叫卢西奥,非常感谢你救了我。”
一旁的陈今越立刻提出抗议:“抱歉,出于礼貌,请问两位是否可以用汉语交流?”
“哦,当然,当然,我会讲中国话!”对方从善如流,尽管这中文讲得十分蹩脚,“你好,我的中文名字是陈显华。我是华裔西班牙人,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。”
“显华,华裔西班牙人。”刘清宁翻译。
阿青婆生于民国初年,长于战争年代。具体的时间没有人记得,应该是1930年以后,她嫁到云上村,没几年,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那个年代,农村的日子并不好过,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几年,阿青婆的丈夫,陈显华的爷爷陈定为了谋生,丢下家中的妻儿,跟着同村人一起去了欧洲,从此音讯全无。
那个年代青田人出国打工,并不走正道,死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数。
阿青婆等了又等,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,村里人都默认他已经死了,还有人劝她趁年轻改嫁,但阿青婆始终没有答应,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养大。
那是个战争的年代,除了应对自然灾害,还要提防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日军的飞机炮弹。
1942年,日军攻陷青田,云上村虽然偏僻,但没能逃过日军的搜掠。
“我父亲上了年纪之后,身体不好,常年卧病在床,常常同我讲起以前的事。”
那时陈建明已有八九岁年纪,他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搜掠,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躲进屋后的地窖里,年幼的妹妹忍受不了地窖的湿闷,大哭起来,引起了鬼子的察觉,
母亲拼命捂住了妹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才逃过一劫,等鬼子走了之后才发现,因为捂得太紧,妹妹已经闷死在母亲的怀里。
当时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,直到多年以后提起来还心有余悸,而母亲因为闷死了妹妹而愧疚,精神大受打击而病倒。
但即便病倒了,她还是得拖着病体下地干活,挣钱来奉养公婆,照顾两个儿子。
可以想见,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,阿青婆过的是怎样艰辛的苦日子。
后来,红军打跑了鬼子,解放军渡过了长江,成立了新中国,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,大约是五十年代,阿青婆收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消息,原来陈定并没有死。
“这事村里人都知道!”李阿四说,“那年我还是个小后生,听我娘说,村里回来个华侨人,是阿青婆的男人,有钱呢!啊哟,不得了,穿西装,打领带,皮箱里都是洋货,后头那座石桥,就是他捐的钱修的,桥头碑上还有字嘞!嘿!原来那就是你阿公!”
那时云上村的人才知道,当年虽然陈定的目的地是欧洲,可是他上错了船,糊里糊涂地跟同村人分开,孤身一人被带到了南美,最后在巴西上了岸。
在巴西,他做过一段时间提包挈卖的营生。
所谓提包挈卖,是海外青田人积累资本最原始朴素的方式。
扛着一个编织袋,装着鞋子、衣服等杂物百货,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。那时候闯天下的青田人,没有人脉,没有门路,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活开始干起。
在提包挈卖的那段日子,陈定认识了一个当地华人的女儿,很快和对方坠入爱河,缔结婚姻。
在新岳父的资助下,两夫妻到了西班牙,开了餐馆,做大生意,赚了不少钱,成了大老板,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阿青婆是什么反应,已无人知,但不难想象。
陈定在云上村住了半个月便走了,这一走就再没回来过。
后来陈定写信来,问阿青婆是否愿意出国,阿青婆拒绝了。
她收下了陈定寄回来的钱,推倒了陈家原本的破牛棚,重新盖了房子,便是现在的陈家老屋。
建新房子的时候,阿青婆只给自己在一楼留了房间,东西两侧各起了二层小楼,留给两个儿子一人一栋。新房建成,又大儿子陈建明娶了老婆,生了一儿一女,阿青婆的脸上,日日都是喜气。
她还有儿子、孙子,村里给她分了地,有田种,有饭吃,日子蒸蒸日上,没了男人,不算什么。
好景不长。
五十年代末,全国上下遭遇了大饥荒,到了六十年代初,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
为了谋出路,陈建明带着妻子和弟弟,搭路子出国投奔父亲,也在西班牙定居,只留下五岁的大儿子和三岁的女儿,也就是陈显华的大哥大姐给阿青婆抚养。
阿青婆不得不又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职责。
70年代末,两个成年的孙子孙女也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。从此,老房子只剩下阿青太一个人居住。
“一直到新房子变成老房子,然后在这房子里孤零零地去世?阿青婆真是可怜。”刘清宁说道。
“其实,我父亲也想接她到西班牙一起生活。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做了,在我十多岁的时候,奶奶来过马德里,还住了一年,所以,我对她有一点印象。”
在陈显华的印象中,奶奶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老人。
她一直穿着很旧的蓝布衣衫,是那种传统的中国样式,衣领袖口还绣着中国样式的花纹。
她不会说普通话,更不会说西班牙语,而是讲口音很重的青田方言。
那时候,陈显华不会青田话,如听天书一般,根本无法与奶奶交流。
阿青婆被接到马德里的时候已经年迈。
那时候,陈显华的祖父已经去世,他的继奶奶是陈家的大家长,在马德里,她唯一认识的只有自己许多年未见、并不熟悉、忙于生意的两个儿子和由自己抚养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。
听到这里,刘清宁忍不住想起了刚到马德里的自己。
当初登上前往西班牙的飞机,阿青婆肯定和她前往马德里之前一样,是对未来的生活抱着一种期待的,她盼望的是与从未谋面的父亲、分离多年的母亲的重聚,期待的是父母疼爱的怀抱,阿青太盼望的、期待的则是母子团聚,一家团圆,从此颐养天年。
但很显然,她们都没能如愿以偿。
父母疼爱的怀抱,是属于她的弟弟妹妹的。而一家团聚颐养天年,则是属于那个抢走阿青婆的丈夫的女子的。
长久的分离,文化的隔阂,是她们和家人之间迈不过去的鸿沟。她们都成了这个家庭的“旁观者”,就像西方电影里那种死去之后留在家里的亡魂。
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愉快。
刘清宁没能追上王静一起去,等到表姐吴楚楚过来接她赶到医院的时候,外婆王永梅已经从急救室出来了。
医院的惨白色灯光永远让人心底茫然。
去医院的路上,刘清宁想起从前和外婆相处的点滴,大部分记忆都已经模糊,只记得外婆对她和表姐这两个外孙女分外疼爱,每年秋天,老屋后门的两颗板栗树成熟,收下来的板栗,总会仔细挑最好的,藏起来留给她们。老屋周边还有几棵柿子树,柿子不耐储存,就晒成柿饼,收起来等她们放了寒假来吃。
还有五月的枇杷,六月的杨梅,一别十三年,再没有吃到过外婆特意留给她的果子。
“外婆为什么要喝药?”她想不明白。
吴楚楚一脸凝重,没有直接回答:“还不就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,老嬢嬢一时想不开。唉,说来话长,不过都是长辈的事,我们别掺和。”
刘清宁想了想:“跟二舅家的事有关?”
吴楚楚沉默了片刻,“嗯”了一声。
两人同时沉默了下来,耳边只有呼呼的晨风卷进车里的声音。
亲戚们闻讯而来,已经把王永梅的病床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,王向远根本挤不进去,耷拉着脑袋,蹲在病房外不说话。
这个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,在老家村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男人,年逾六十,头发花白,脸上、粗粝的手上,都布满与其年龄并不相符的皱纹,整个等待的过程中,沉默木讷。
医生出来的时候,两个妹妹和弟弟都呼啦一声围了上去,七嘴八舌问东问西,他却始终站在外面,竖着耳朵凝神仔细听医生的话,双眼却是迷茫涣散的,显然,他并听不太懂医生在说什么。
弟弟王向高,年轻时候就携家带口去了深圳做生意,见过一些世面,只比王向远小三岁,却是截然不同的模样,虽也双鬓发白,但穿着西装裤,polo衫,蹬着一双皮鞋,头发、皮肤都散发着一种油润的光亮。
王美莲站在稍远的地方,在跟远在国外的大哥通电话。老大王向松在南美,小日子过得也不错。几个近亲都到了,只是徒劳地或站或坐,时不时地搭上一两句话。
此刻谁也不能做什么。
刘清宁一到,就被一堆亲戚塞到了病床前,王静的身边:“快看,宁宁来了。”
王静因为远道而来,又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回国,得到了病床边最核心的位置。
床上虚弱的老人睁着混浊湿润的眼睛,茫然地朝着清甜看来,目光久久地定着,布满皱纹的脸上没什么神情,只有嘴角微微地颤动着。
刘清宁没想到一别十三年,再见外婆竟然是这样的场景。
记忆里的外婆,穿着蓝布衣衫,半花白的短发总是梳得很整齐,用两个黑色夹子别在耳后,精神矍铄,每天一大早去村口的老人活动中心搓麻将,非得搓到外公板着脸找来,才迈着小步子急急忙忙回家做饭。
而此时,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头发已经全白了,也稀疏了,此时因为一番折腾,已凌乱不堪。医院的病床不过一米宽,年迈的老人陷在发黄的被褥里却还空余,她瘦得仿佛只剩了一把骨头。
刘清宁的鼻子一下就酸了。
有人在背后推她:“叫外婆呀。”
可她张张嘴,曾经熟悉的两个字却卡在了喉咙里,嘴巴紧紧地闭住,仿佛涂了胶水一般。
好在并没有人坚持为难她,话题马上就转回到了王永梅身上。她在无人留意的情况下,退出了病床边的核心区。
一个和外婆年纪相若的老太太站在床对面,拍着外婆的肩膀,扯着嗓子中气十足:“儿女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你面都没见着就走了?”
这一问把老人蓄在眼眶里的泪全拱了出来。
刘清宁真怕她手劲太大,一下子把外婆给拍散了。
病房里人多,刘清宁退到走廊里。她目光张望,瞧见吴楚楚正站在护士站前,跟护士说着什么。她的身边站着一个男人,挺拔,清瘦。
“姐!”刘清宁走过去。
两人同时回过头来。
“见到外婆了?”吴楚楚问,将身边的咖啡递过来,“喝杯咖啡提提神,我朋友买的。”她指了指身边的男人。
对方朝她一笑,点头招呼,正要说话,手机响了,接着电话匆匆离开。
吴楚楚望着那背影,半开玩笑:“大领导,就是忙。”
四月的清晨,还有些冷。刘清宁坐在凳子上慢慢将一杯热咖啡喝完,精神才略略振作一些,医院里的脚步声也渐渐多起来。
一场令人期待的团聚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被提前了,但气氛并不愉快。
喧闹了一个上午,亲戚们来了一拨又一拨,流程大致相同,先看望了阎罗殿走一遭回来的老人,讲了一些大同小异劝慰的话,然后又拉住王静寒暄几句,轮到刘清宁的时候,一律都以“都长这么大了”开场,然后说一些她小时候的事,以“你还记得吗”结尾。
这些事,刘清宁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印象,但眼前的人,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了,但她也只能说:“哦,记得记得!”
也不管她是真记得还是假记得,得到这个答复之后,对面的人便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,就此放过她。
末了,再约定王静什么时候上他们家里吃饭,回过去再劝慰老人几句,便正式结束了一次探视。
到了中午,两母女实在撑不住了,王美莲就让吴楚楚先送她们两个回酒店休息。
等她们走了,王美莲又安排王向远:“哥,等晚上楚楚下班,我让她去接阿静两女去我家,吃了晚饭,再让她送你回村里,妈这里晚上我看着就行。”
王向远“哎”了一声答应了。他平常就没什么主意,虽是哥哥,但对这个妹妹的话言听计从,在他的眼里,自己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人,一辈子在村子里,连市里都没去过几次,兄弟姐妹几个,都比他有出息,走得远见得多,他们懂的肯定比自己多。
探病的亲戚走了一波又一波,但似乎谁都没留意到王向远,虽然是他第一个发现老人家寻短见喝了药,是他把老人家送到了城里来。
怎么发现老人家服药,怎么敲开了驻村干部的门,怎么灌肥皂水催吐,把老人家一路送到医院......都以王美莲作为“发言人”,一一向亲戚们讲述交代。
没人注意到这个如木头一般坐在门口的“当事人”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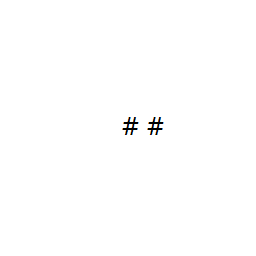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